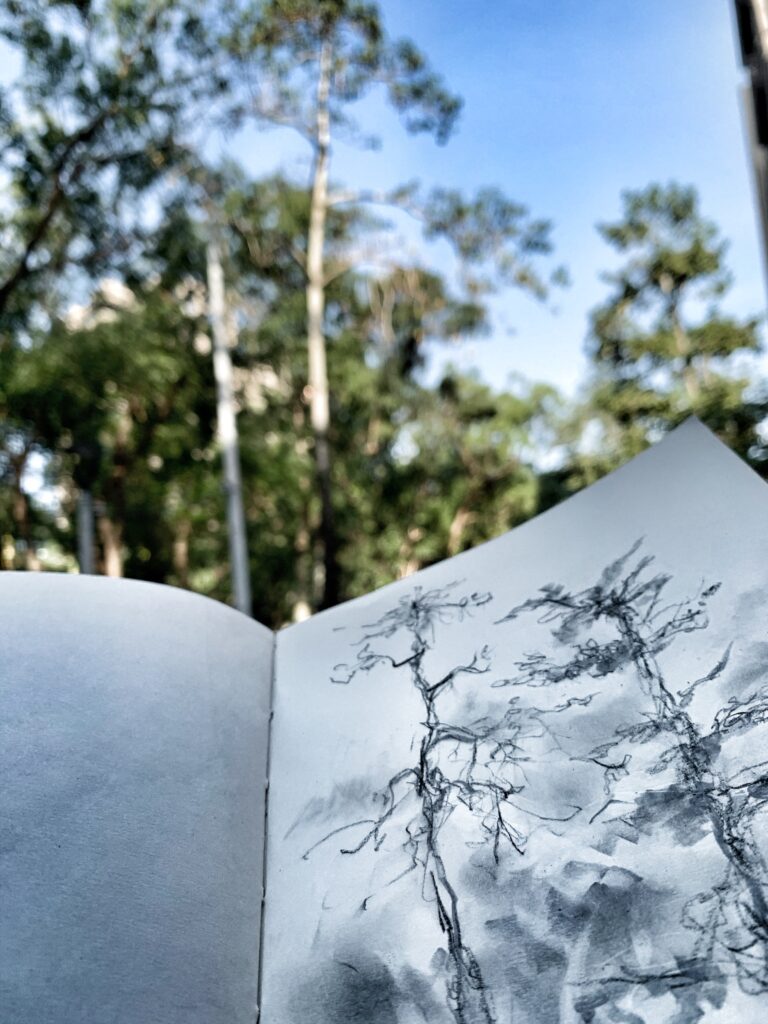【中正紀念堂】
1884年清治台灣巡撫劉銘傳建台北城,東門城外駐守著劉巡撫的淮軍班底銘字軍定海營,算是台北城衛戍部隊的開山地基主。
1904年日治總督府拆台北城,拿城牆青石蓋了台北刑務所的高牆,高牆外大清帝國營地入駐了日本帝國新編台灣軍步兵第一聯隊與山砲隊。
1949年國民政府遷殖島國,陸軍總部,聯勤總部,憲兵總部聯合入駐,來自大海彼岸的將星再度雲集此處。
1972年,反攻宏圖暫停,且不知何時重啟的陸軍總部南遷桃園龍潭,此處原規劃為國際觀光旅館與世界貿易中心(對,就是後來更東邊的信義計劃區),但三年後的春夜雷雨大作,一個改變中國與島國歷史的人物迎向了命運的終點,也小小改變了此處的命運。
「頭戴青天白日冠,手持青龍偃月刀」,少年時與舊書攤邂逅的女孩相約此處,初見黨國陵墓時,想到的竟是小時「雲州大儒俠」中,民間謡傳布袋戲大師與黨國交易後登場的神秘人物「中國強」。
到「野百合運動」,數千學生群集此處,要求渡海而來的老法統們再不能扮演代表島國民意的角色時,此處已被稱為「中正廟」了。
既稱「廟」,祭祀的自然是「神」,對跟隨著他渡海而來的族群而言,他的地位或與「神格」無異。
多年後,翻閱他解封出土的少年日記,看著不時會出現的,掙扎於人性的句子:
「下午,出外冶游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
「今日邪心勃發,幸未墮落耳。如再不強制,乃與禽獸奚擇!」
「晚,外出游蕩,身分不知墮落于何地!」
「介石!介石!汝何不知遷改,而又自取辱耶!」
忽而想起自己少年時那些無法入眠,騎上單車踩遍一整座台北城的漫漫夏夜。

【南門市場】
1904年,只存在20年的台北城拆除,隨著蜿蜒清澈的瑠公圳溪水而來的南門城外,景象忽而開朗遼闊,城南外的泉系與客家農戶,天沒亮便將作物運抵此處,在隴畝間坐地擺攤,俟城內的主婦婢廚前來採買灶腳所需。
1907年,新店溪畔的台北州水源地工程接近完工,潔淨安全的水道水與地下排水系統已牽設至此,殖民者建起了一落紅磚長屋,將原先散落的攤商遷置入內,避免了雨打日晒,也保障了食材衛生。
殖民者剛在城南沿河畔,興建了讓渡海而來的內地軍公教家屬落戶的川端町、佐久間町、兒玉町、新榮町…町町相連,這座殖民者用來示範帝國文明的現代市場,特許和漢共處(隔年興建的西門町新起市場,則是只許日本人專用的內地貨與舶來品市場),由於座落於千歲町一丁目,故名「千歲市場」,是為南島第一座現代化市場。
1949年,國府遷殖南島,大批江浙財政官員接收了原總督府日本官員在城南的宿舍;昔日和漢共處的「千歲市場」,遂也在吳儂軟語與鏗鏘越聲中,逐一端出了糖蓮藕、寧波年糕、酒釀湯圓、湖州粽、上海鬆糕、肝臘腸、手工湯圓、南京板鴨與金華火腿..…,成為今日有江浙廚房之稱的「南門市場」。

【華光社區】
「欸,這一次啊,搞不好,就他奶奶的讓哥兒們給矇上了?」
冬日清晨的村口新鮮豆漿店,熱氣氤氳中,眷村男生狠狠咬了一口剛出爐的燒餅油條,眼睛瞇著笑意希望,口齒不清的說。
……
1987年,剛自金門海哨站了一年十個月退伍,好友介紹,在這座昔日台北刑務所官員宿舍的破落屋群中,租了一個日式偏廳安身。
月租三千,衛浴共用,四五個男生擠一個當年日本人家院落,半夜尿急,敲門有人,自愛些出門左轉再右轉到村子邊角公共廁所撇條。
那時代剛退伍的男生身子很難不精壯,因為喘不過氣,跑不了五千公尺,士官長就逼練仰臥起坐,拿到退伍令那天就做了226個,此後再也不能。
某日下午,同住朋友有位老大哥來訪,睨了我一眼,說這位小兄弟漢草不錯啊?晚上請你們吃飯,再陪我去信義路信維市場拜訪個老朋友?
朋友神色略異,滿臉堆笑,說唉這怎麼好意思呢?老大哥揮揮手,毋庸再議。我還沒找到工作,有人請吃飯當然不會反對。
直到我們在信維市場四樓老舊的公寓客廳苦等兩個多小時等不到老大哥口中的「老朋友」回家,在午夜的市場騎樓下揮手告別,看到朋友鬆了一口氣時;才意識到,自小被人追債的我,竟也幫人做了一回討債圍事的工。
那時高速公路已通車十年,開始維護保養,某夜在養工處當差的大男生下班後來此小酌打屁,趁著酒意笑謂:
「哎,那個南下幾公里到幾公里那段你們有開過吧?斜坡。斜坡喔?他媽的保養到下雨就會積水。哪個單位包的?下雨就會積水?小永公司包的。」
然後大家就哄堂大笑,好像剛過世不久的今上小兒子,是跟他們在眷村裡一起鬼混長大的哥兒們。
……
印象中,那是我最後一次跟眷村男生一起在豆漿店共用早餐,隔年他老弟要漲房租500元,我就另覓他處了。
很多年後,每當我聽到有人用類似的口氣說:「欸,這一次啊,搞不好?」,心中就浮現一絲不祥之感。
沒有一次。我親愛的老友啊…沒有一次搞得好的。
我們只是在那個年代,一次又一次的拿青春去賭機遇,然後一點一點耗失掉,人生僅有的一些些運氣。

【殖民地台灣軍司令官邸】
1909年,台北州水源地工程完工,殖民者著手自台北城南開始現代化,舊南門城外攤販已在兩年前遷入了紅磚長屋的「千歲市場」,總督府營造設計師森山松之助也為看似級別不高,但角色至為重要的「總督府土木局土木課」課長高橋辰次郎營建官舍,以表總督府最大的感謝與重視。
高橋課長帶領著包括被稱為「台灣水道之父」的濱野彌四郎與開建「嘉南大圳」的八田與一等帝國技師群,在這座位於記念力爭台灣不售予法國,帶著後藤新平改變台灣的兒玉源太郎總督所命名「兒玉町」的豪宅住了沒幾年,便回日本了。
高橋之後,再沒有一位課長有那個份量入住這棟豪宅。
然後這棟豪宅便成為歷任總督巡視水源番域如新店烏來時回程休憩的別邸,也是皇室貴眷來訪南島時的居所。
大戰爆發,此處因鄰近台灣軍司令部,自然成為台灣軍司令官邸;1947年國民政府接收托管南島,由非黃埔系出身,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的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入住。
孫立人駐在時,官邸中外賓客絡繹不絕,大廳堂招待著大學教授,民國文人;小房間密談著反攻規劃,國府前途。
1955年,孫立人被國府特務指控接受美國指派,密謀推翻蔣氏政權,另立台灣軍政府。旋即被押往台中軟禁,隔離舊部,乃近終生。
此後,這座豪宅再無官員權貴敢入住。
傳聞大戰末期,台灣軍司令官指示將大量軍餉黃金埋於此處。
又謂1945年8月15日天皇玉音放送時,有一批皇軍軍官在此切腹,自此守護著在另一平行時空將被啟用復國的黃金寶藏。
而忠心不泯的軍國鬼魂與黃金,向來是殖民島國從不缺席的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