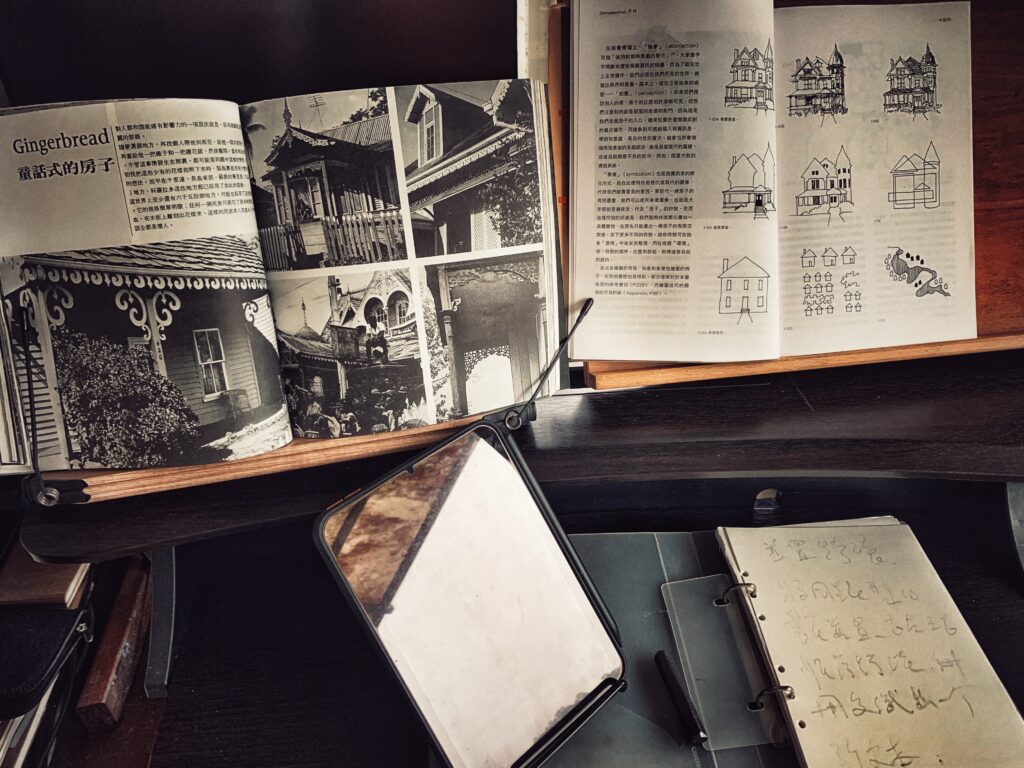Sunflowers in spring, Taiwan
Sunflowers in spring, Taiwan
「最文明的群體最容易因私智而滅亡,因為徹頭徹尾的理性是德性解構的結果。」
—-劉仲敬.《經與史》
 Sunflowers in spring, Taiwan
Sunflowers in spring, Taiwan
這場積累多時,突而炸裂的春鬥,衝撞了島國多年來所相信不疑的事物:
一.自由經濟?
暫不論「反服貿」是否等同「反開放」(這是官方論述的主策略),完全開放與自由市場是否就是島國唯一的選項?
完全開放下的自由市場,就得選擇在國際分工中扮演單一角色,是否就得放棄某些事物,如小農經濟,與由此而來的有機農業?
(樂觀者也可說,島國將成為大中華地區最大的有機農業輸出地)
至於「全球開放必得先向中國開放」的官方論述,是現實還是邏輯,則可另論。
二.代議政治?
島國人民經歷百年來的殖民與黨國統治,好不容易掙來的民主代議政體,卻在短短三十年間,成為代議分贓政體。
當代議委員在電視上直言:「那就是個交換場合嘛!」
當學運領袖在議堂中開口:「總統,請接受人民的指揮!」
我們都被迫思考,誰是人民?誰能代表人民?
誰又從人民的信任中,取得最大的利益?(家族資產或歷史位階)
三.世代交替?
1945~1964年所出生的戰後嬰兒潮,到現在是70歲到50歲的在位者了。
這群人在幼兒時,全球最大的公司是生產奶粉的雀巢(或味全?)。青少年時,是賣他們糖水的可口可樂(或賣速食麵的統一)。成年時,是每個人都要開部車的通用(或每條巷口都有的小7);現在,他們還在職場的位子上,也在成長中置產,取得島國多數的土地。
社會資源與資產,大多牚握在他們手上,只會繼承,不再流動。
這群人身處戰後大成長潮,相信「愛拼就會贏」,相信「有錢才是贏」,也相信他們成功經驗一定能複製到下一代,後照鏡中看到的過去就是前方不變的路。
島國在戰後的成長,就是「依附政治」+「代工經濟」。
以前依附美國,全球代工;現在只要依附中國,更可以透過中國當全球工廠的工頭。這不是很簡單的邏輯嗎?為何小朋友聽不懂?
四.中國因素?
除了血緣由來,「文化中華」構成了上一代島國人民的認同來源。
島國上一代的統獨爭議,多陷在此二者間論戰。
但在島國出生的下一代,血緣多元,而「泱泱中華」,只是他們的文化選項之一。
他們更在乎的,是基於本土的生活方式,與對岸社會價值的落差。
兩岸開放往來後,有了強烈的對照組,更加強了新一代的島國認同。
「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是好國好民。」
這一句話,不止表明了對未來的期許,也隱含了對過往所信仰的,那個「天朝中國」的否定。
五.資訊輿論?
春鬥初始,資訊紛雜。不多時,島國便有平行時空之謂。
初以資訊來源為二分:「看電視,聽廣播,看報與鄉里口語」v.s 「BBS,臉書,Line與社群直播」。
資訊的目的在取得認知,改變或堅定認同。
當佔據議場者直播如何垃圾分類時,也是在意識到在全國人民注視下,以行為改變官方的「暴民認知」。
抗爭者與官方都在打一場輿論戰爭,都在取得自身的合理性與對方的不公義。
這樣的結果,就反應到臉書上。
3月18日到3月23日傍晚,島國臉書逐漸呈現「表態」的壓力。
至3月23日深夜,直到3月30日,便近乎「全島攤牌」了。
3月30日以後,大家各自碰觸到彼此的邊界,有人不再往來,有人不再模糊,有人保持沉默,有人容異的厚度與反思的深度不再如往。
能量漸息。中正一分局的衝突,只是之前委屈者的能量釋放。
甲午春鬥之後,很多事不會再一樣了。
「鬥」,是指想法不一樣,價值不一樣,路線不一樣,才會有衝突。
「爭」,是指,彼此要的東西都一樣,不是你的,就是我的。
「鬥」是春秋,圖的是大義名份。
「爭」是戰國,要的是國土人民。
「鬥」之後,通常會走向「爭」。
 Sunflowers in spring, Taiwan
Sunflowers in spring,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