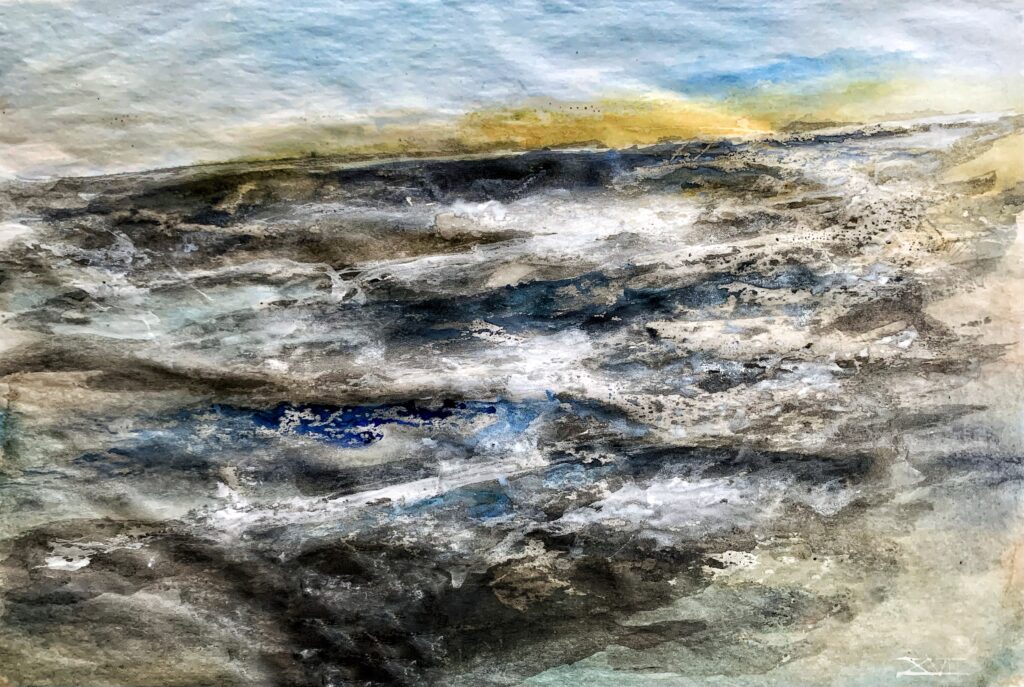【隨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
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
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周易本義[宋.朱熹撰]》

「你說:”就算是上帝,到了第七天,也得休息一下,讓下一個週期的黎明前來喚醒世界”?」
「是的。」
「那我如何知道何時是黎明?或者,黎明前夕?我好作準備?」
「上層掌握權力者發生變化。」
「為何不是下層我們這些每天在做事的人發生變化?」
「下層做事的人每天都在運動變化,但通常不容易看出是系統的慣性運作,還是結構的鬆動位移。
但上層掌握權力的人必須維持穩定運作,一旦發生變化,即便是和平交接,也會帶來不可預知的歷史路徑偏移。」
「那這時像我這種位於結構底層,權力邊緣的人,應該幹嘛?」
「平常該幹嘛就幹嘛,不要特別去做什麼,也不要特別不去做什麼;維持穩定的能量蓄積,就是你最好的優勢。
如果你過早去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會破壞長期以來維繫的貞定穩態,讓你的優勢反轉為劣勢。
同時,因著你改變了自己的狀態,反而讓上層權力持有者心生不安,讓你捲入未知的風險威脅。」
「那我就一切照舊嗎?」
「在一切照舊的例行事務中,可以逐漸增加某些事務的次數,讓它的比重增加。」
「什麼事?」
「出門跟與你平行的外部其他單位交易資源,交換資訊,慢慢形成一個利害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