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詞n,是靜止的,指涉一種存有。
動詞v,描述一個在時間中流逝,在空間中經過的無常。
Was(已是),一個空杯狀態的動詞。
身處當下,但什麼都不是。
故此接受身邊任何事物,成就意義,成為已完成的必然消逝。


名詞n,是靜止的,指涉一種存有。
動詞v,描述一個在時間中流逝,在空間中經過的無常。
Was(已是),一個空杯狀態的動詞。
身處當下,但什麼都不是。
故此接受身邊任何事物,成就意義,成為已完成的必然消逝。


「遵循規則,不是我的優先選項。」
——法蘭克.《紙牌屋/第一季最終章》

「我們如何擺脫像國族、宗教這種外來”觀念基因”的強行寫入?」
「不要對抗,只需觀察。」
「觀察那些外來觀念如何寫入嗎?」
「不。外來觀念威嚴如父,慈愛如母,寫入時一定是妳心甘情願而不自覺的,所以妳也無從觀察起。」
「那我要觀察什麼?」
「觀察自己。」
「我們如何觀察自己?」
「觀察自己是否如棋盤上的棋子一樣,已被設定好固定的角色與規則?
如果妳覺得自己不過是小卒士兵,過了河,自然會覺得無路可退,死命向前。
如果妳以為自己是天馬飛車,自然會橫衝直闖,侵門踏戶。
如果,妳認為自己是將帥君王,自然就會端起架子,謹言慎行,遇到突如其來的危險時,合理的要別人為自己犧牲奉獻。
觀察自己是否在扮演某種約定俗成的角色,遵守某種通俗劇情的發展,是逃離棋局的第一步。」
「然後呢?」
「當妳意識到自己只是在棋盤中扮演某個棋子時,妳的視角自然就會從身在局中,逐漸往上拉高,成為居高臨下,觀察棋局的人。」
「你是說,成為棋手嗎?」
「不一定。要能破壞,進而改變規則的人,才會變成棋手。我們得先成為旁觀者,才有機會跳脫棋子的命運。」
「當我們擺脫外來觀念的寫入,不再認同約定俗成的角色,從局中的棋子成為旁觀者時,我們會得到什麼?」
「妳不會得到什麼,妳只會失去。
妳會失去身份,失去角色,失去相信的事物,失去依循的規則。
妳會失去所有來自神的幫助與祝福,承擔一切來自自己行為的後果。
然後,妳才會回到出生之前,尚未與這個世界發生關係前的,那個狀態。」


「你去金門的那一年夏天,好長。有天下午,杭州南路的蟬鳴叫得人都快瘋了…」她點了一根短短的高盧藍煙,掂著長長的指尖,淡淡笑著。

1986年,冬天,深夜。
她在她新租的,城市南方的舊公寓,煮了一壺咖啡。
那是我離開台北快兩年後,第一次回來。
在金門東線海邊,站了兩百多個夜哨後,習慣了在應該換上裝備,到槍櫃取槍上子彈的時刻;卻人在台北,啜飲一杯老友煮的咖啡,忽然覺得不切真實。
1984年那會兒,持續了一整年的,在杭州南路的派對已然悄悄走入尾聲。
劇團還在,但人與人的角色已然換上下一幕,有些人好在一起了,有些人沒辦法再好下去了。
她忽然說起前一年的事,說的像是十多年前的青春。
「我們三個女生,有人起了閧,好熱,咱們去花蓮泡溪水吧?」
她笑得眼睛瞇成兩條長長的魚尾:「三個女生去有點怪,想要捉個男生當挑夫,可你又去當兵了,她就說,唉那個誰誰延畢,還在陽明山上蹲著,就找他一起去吧?」
我啜了一口咖啡,安靜聽著我缺席時的,朋友的青春。
「就這樣組了個三娘教子團,坐著夜車去了花蓮。」
她吐了個煙圈,繼續說著:
「到花蓮時天亮,東海岸的天空藍的不像真的,我們改搭公路局的車子,直奔溪邊。
三個女生換了泳裝,就往溪裡頭走,愈走愈涼,可不知為何,心裡頭反而發熱…。」
我看著落地窗外,依著公寓陽台長的樹叢,在冬夜裡隱約搖曳,一邊想像那個夏天裡,她們泡在花蓮泌涼的溪水時,我在金門幹嘛?
「他被我們扔著岸邊打理烤肉的事,她忽然起了意,說,噯,我們來做些壞事吧?」
她們高呼著他的名字,叫他快來。他莫名其然,以為發生了什麼事,小跑步涉著溪水就來了。
俟得他近時,三個將身子埋在溪水裡,只露出雪白頸首的年輕女子,像神話傳說般,忽然在凡間男子面前露出真容,三人一起站起來,身上一絲不掛。
「他嚇壞了。」她嘿嘿笑著,「好像是他做錯事似的,低著頭,不敢看我們…。」
她按熄了快燒到手指的高盧,忽然有些落寞:
「他不知道,她是喜歡他的,從一開始就是。喜歡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拉著我們另外兩個女生,讓他看個明白。」


「有信仰的人通常比較喜歡自己是正確的,而非慈悲的。
他們也常難以捨棄自我中心,需要宗教來背書自己的自尊自大以及個人認同。」
─Karen Armstrong,曾為修女,後成為比較宗教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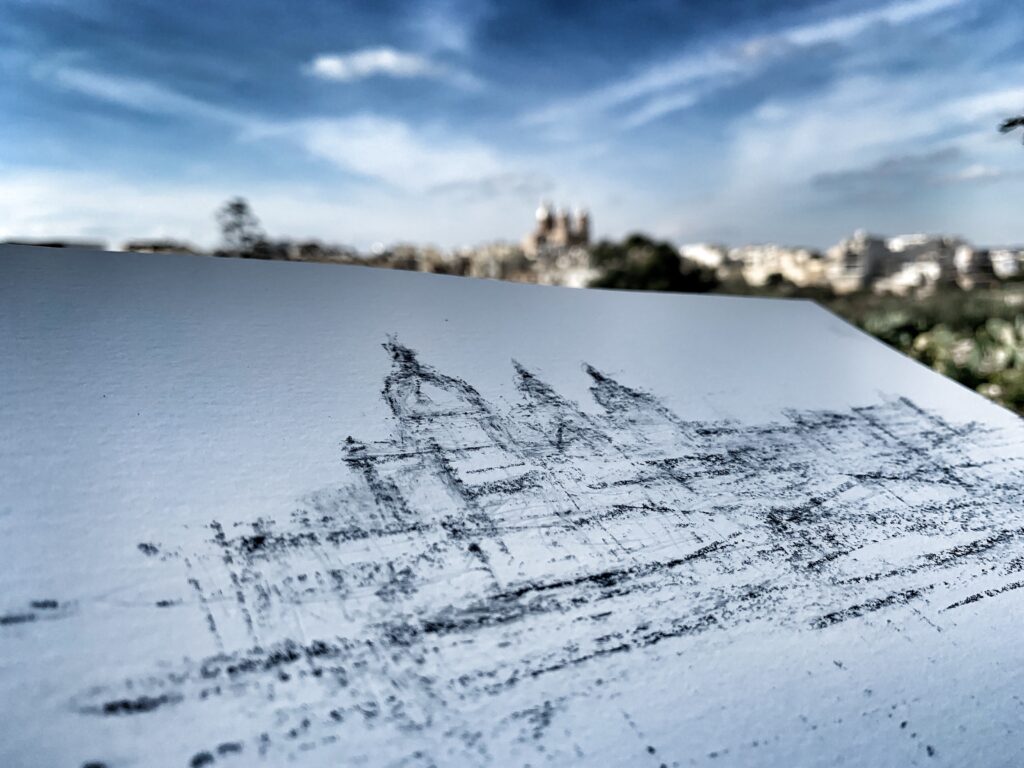
「所以,有理想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人嗎?」
「我想不是的。理想與信仰,其實是兩回事:
信仰是指相信一種已知的價值。
有信仰的人,會用這種價值,來比對世間事物,作為他們對待這些事物的態度與取捨。
在這個比對與取捨的過程中,他們也同時把個人與這種價值合而為一,取得讓自己可以安適與居高臨下的好位子。
他們容易把世界視為一種黑白分明的靜態系統,躺在他們面前無法動彈,等著他們透過一種簡單的認知與行動,改變一切,讓世界更美好。」
「簡單不好嗎?」
「自己活得簡單而不假外求很好。但無視於世界是一個複雜多元的動態體系,強行以神意或善意為名侵入,卻常常帶來讓別人哭笑不得的災難。」
「那理想主義者呢?」
「理想主義者,永遠在已知的事物中,尋找一種他們猜想有,但不確定那是什麼的,未知的『理型』。
他們時刻戒慎恐懼,知道自己尋找的,不一定是別人想要的。
他們在世間諸般事物裡,向上求索共同的本質,向下辨識不同的差異,經歷無常,身不由己;時而高峰獨攬,時而低微窘困,感受一次又一次的豐美與荒蕪,至死前一刻,都還在尋思疑惑,跌撞不得的旅途上。」
「聽起來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而那些尋找理想的人是自找苦吃?」
「是的。如果你想要的只是幸福,那妳應該早早找到信仰,讓自己融入那個平安喜樂的大家庭中。」
「那你呢?幸福不好嗎?」
「幸福很好。我只是無法相信,交出相信就能得到的幸福;也不認為,生命是為了追求幸福而來。」
「那理想主義者尋找的,究竟是什麼東東啊?」
「理想主義者,終其一生,只為尋一個不受惑的人。」


「自願的將自己交付命運女神,讓她隨其所意,將你的線紡成無論什麼吧。
一切,都只需堅持一天。那記得的人,與被記得的事物。」
——Marcus Aurelius.《沉思錄》

有本日文雜誌,我很喜歡,刊頭大大的三個毛筆漢字:《一個人》。
創業以來,慢慢學會一些事:
聽所有人的意見。
跟少數跟你思維不一樣的人討論。
自己作決定。
一個人時,不用為了對抗或附和別人,而迷惑了自己本然的初心。
一個人時,對自己坦然而現實。
今天,我一個人。
08/30/2013-麻六甲海峽


「Walk, don’t run!」
—-Roman Polanski的父親。在全家被迫搭上往納粹集中營的列車時,趁混亂讓年僅五歲的兒子逃離時的耳語。

「你說”理想主義者,在處理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事物之前,要先學會處理自己的欲望與情緒。”,是指我們應該不帶欲望與情緒去面對這個世界嗎?」
「不是。如果我們沒有欲望與情緒,就不會有能量與動力去面對這個世界了,更何況處理?」
「那你所謂的”處理”是什麼意思?」
「覺察自己的欲望與情緒,隨時與世界作碰觸比對,找到自己的角色與限制:
世界無時不在流動變化,我們再怎麼理性觀察,都只是站在水邊而不敢下水,無從體會水的冷暖與衝擊,看到的也都是光影的折射,不是實相。
但若妳勇敢的踩入水流之中,因感受而來的溫度與膚觸,就會讓我們有了欲望與情緒。」
「那我們如何使用欲望與情緒?」
「當我們有所欲求,而世界不同意時,就會覺得羞辱尷尬;請珍惜這個尷尬,因此我們才會知道空間的境遇邊界已經發生變化;妳得調整自己的欲望,在尷尬中學會自在。
當我們情緖起伏,而世界不理會時,難免覺得不快彆扭;這意味著時間已改變了世界的虛實密度,和我們因著記憶而預期的反饋不一樣;妳得學會與自己的情緒好好相處,才能安住在彆扭之中。」
「學會在尷尬中自在,在彆扭裡安住,可以幹嘛?」
「世界終究是一列開往終極未知的列車,在列車上的我們,總是因著時時刻刻不確定而焦慮難安。
一個自我訓練有素的理想主義者,卻有機會在這一團混亂中,不引人注意的,帶著她小小純淨的靈識,從車站月台悄然逃離。」


「令生活痛苦難忍的,是細微的捉弄。
我樂意頂著狂怒風暴,奮力前行;但和風徐徐時的一粒微塵,吹進了我的眼睛,便足以讓我焦慮煩惱,裹足不前。」
—-Soren Kiekegaard(丹麥哲學家)

「你是理想主義者嗎?」
「說來可恥。但我猜想,我可能是的。」
「你是說你看待世界都充滿理想,正面積極嗎?」
「不是。妳說的是樂觀主義者,不是理想主義者。
樂觀主義者相信不管如何,明天一定會更好;理想主義者知道,如果我們不做些事,明天會比今天更糟。」
「所以理想主義者不樂觀嗎?」
「理想主義者起初通常是樂觀的,但生活的現實,造化的試煉,會一再剝除他那自以為是的自大與樂觀,直到大部份的人放棄他們原先所相信的事物,剩下一小撮無可奈何的人,只好被迫成為理想主義者。」
「這樣的人,特點是什麼?」
「看世界不順眼。」
「很多人看世界都不順眼啊?」
「大部份人看世界不順眼,只是因為這個世界不合他們的利益與價值;
理想主義者看世界不順眼,是世界沒有進化,沒有創造出新的,比現在更好的事物。
有趣的是,理想主義者因此,得以體認到一件奇妙的事:
這世上其實沒有真正的壞事,只有某人因為某事所引起的壞情緒。」
「什麼意思?」
「所有的事物在時空之間發生,都是來自整體結構的持續變動,但人註定只能站在某個角度某個立場去跟它發生關係,因此而產生利害得失;你的損失,常常就是某人的獲得,所以事無好壞,只有人因得失而產生的憂喜苦樂。」
「所以?」
「所以理想主義者,在處理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事物之前,要先學會處理自己的欲望與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