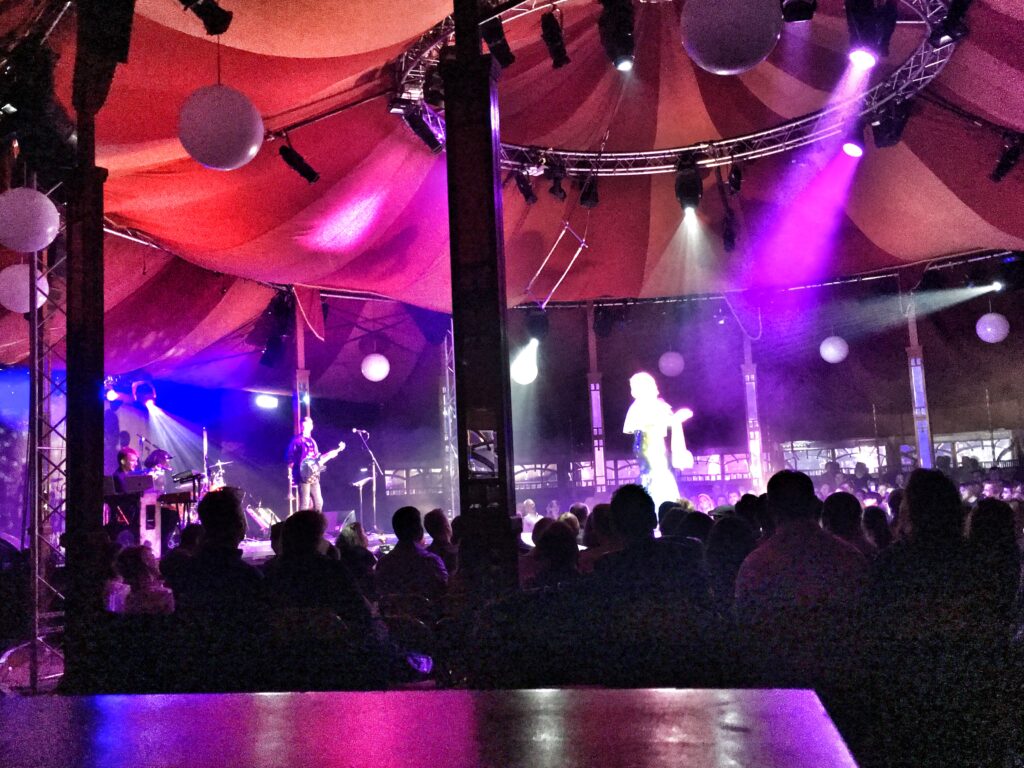「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一切有為法,應作如是觀。」
──藏譯本《金剛聖般若波羅蜜大乘經》

「邊界構成了場所,場所又呈現了事物,事物與我們發生關係,場所才對我們有了意義…但說到底,我們又從場所裡頭得到了什麼?」
「我們從場所裡得到一次又一次,一層又一層,微妙而深刻的體驗。
說到底,這些體驗又回過頭來,構成了當下現在的我。
我還記得,書店開幕那天的華燈初上時,老闆從總公司趕來,偕著我與書店主管,走到對面大學門口,回過頭來,看見書店燈火輝煌,燦爛如星的一刻。
我也記得,就在那天淩晨,我與書店主管在未開幕的書店門口吵了一架,因為年輕的門市已上架18個小時而未休息,我請求開市時間延後至下午但未獲同意。最後是她電召總店店長率領資深門市前來救援,我在一旁無力的看著另一家店的同事幫我上架,感激與羞辱同時而生。
書店開幕那個月,我忙著作前台的行銷促展,忽然被老闆叫到地下二樓的倉庫,才驚覺我的庫存已清空近半,貨再補不進來,前台就空桌倒櫃了…
到了夏天結束時,故人攜著啤酒來訪,我們在打烊後的書店二樓咖啡座,看著深夜的馬路與對街的大學叢林,就著酒意,淡淡交待了當年的一些小小心思…
冬日來臨前,我被調回總店;第二年,我就離開這家後來被稱為人文地標的書店。」
「你還會去這座書店嗎?」
「會,常去,但就是一般訪書者了。
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天光時刻下,會偶然瞥見1996年夏天的浮色倒影,與此刻的現實交錯流動,讓人無法言語,不知如何是好…」
「但你還是沒停下來,一直換下一個場所,追尋不同的體驗?」
「作為一個生命體,哪怕死後形神俱滅,灰飛識散;我又怎能拒絕在死前最後一刻,讓自己持續進化的邀請與誘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