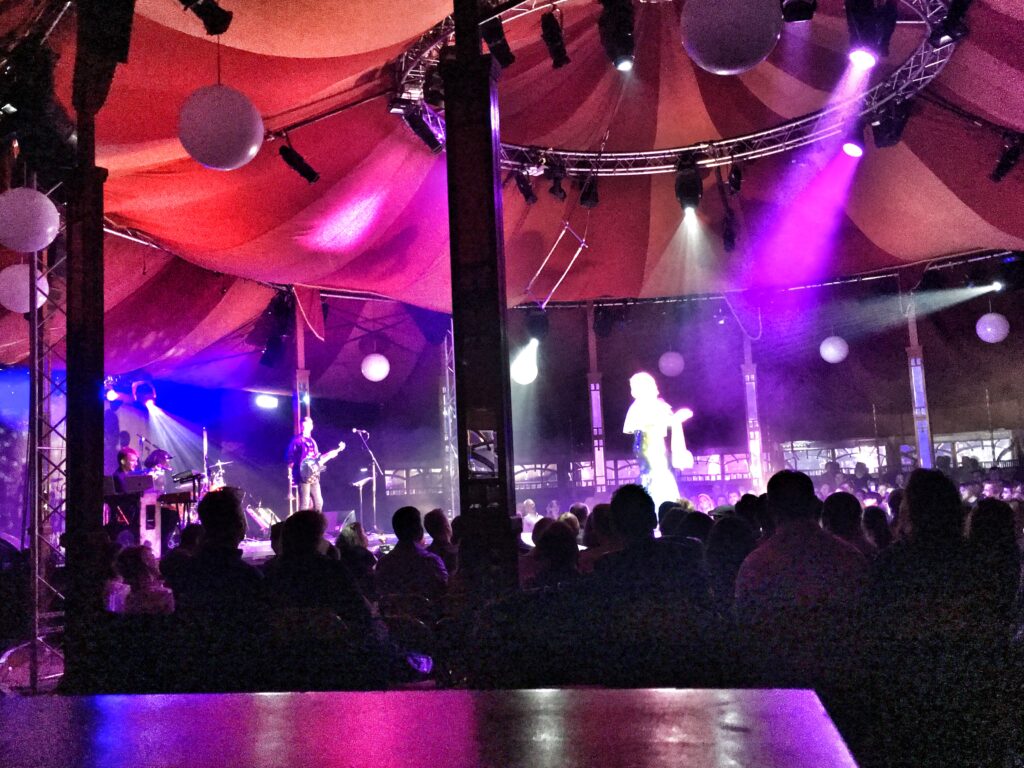「 人類並不懼怕困境,事實上困境能讓人的生命更堅韌強壯。
人類最怕的是” 多餘感 “,而現代社會正在往創造更多”多餘感”的路上大步邁進。」
— Sebastian Junger

「人類由農耕開始了分工與交易,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文明的起源?」
「是的。」
「那你為何又說,文明的曙光之下,每個人都拖著一條長長的陰影?」
「當我們遇到一位陌生人時,彼此會怎麼介紹自己?」
「我們作學生的,大概就是哪所學校,什麼科系的;你們大人,應該就是互遞名片,上面印著公司與職稱吧?」
「對,這就是我們現在認識彼此的方式:我學習、從事什麼工作,所以你意會到我所產出的價值是什麼?也可以立刻判斷,我們彼此的社會角色有無利害相關?有沒有什麼資源可以交易的?有沒有什麼資訊可以交流的?」
「這樣有什麼不好嗎?」
「就促進社會的運作成長而言,當然是有效率的;但要付出代價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異化。」
「異化?」
「嗯,一個彼此被攪拌成群體,與他人生活糾纏共生,但內心卻日益荒蕪孤獨的世界。」
「為什麼生活關係愈緊密,距離卻愈遙遠?」
「因為我們是先成為一個工具,或一組系統的某個零件,再來建構彼此的關係;久而久之,我們也會從別人對我們社會角色的認同,轉化成對自己存在價值的認定。」
「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妳沒有學歷出身,別人就無從辨識判斷妳是誰?如果妳沒有拿得出手的名片,社會就無法理解妳的產出與價值是什麼?
於是妳就會被禮貌客氣的歸納為「對我沒有意義的人」,因為妳無法與這個社會的其他人發生關係。
最後,妳也會認同別人對妳的角色設定,認定自己就是個多餘的人。」
「那我要如何逃離這個困境?到荒野中求生嗎?」
「有人試過了,我不建議這個選項。
妳何不這樣看:如果文明社會讓人心荒蕪,那荒野不就在眼前了?
行使妳的自由意志,拿回主動權,找個自己心甘情願扮演的角色,在這個荒野中取得生存的資源與生活的樂趣。
但,親愛的,小心記得,即便妳不小心做了對別人有價值的事,不留神成為讓人對妳有欲望的人;請不要被人,被自己騙了。
妳仍是那個:”不是妳的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