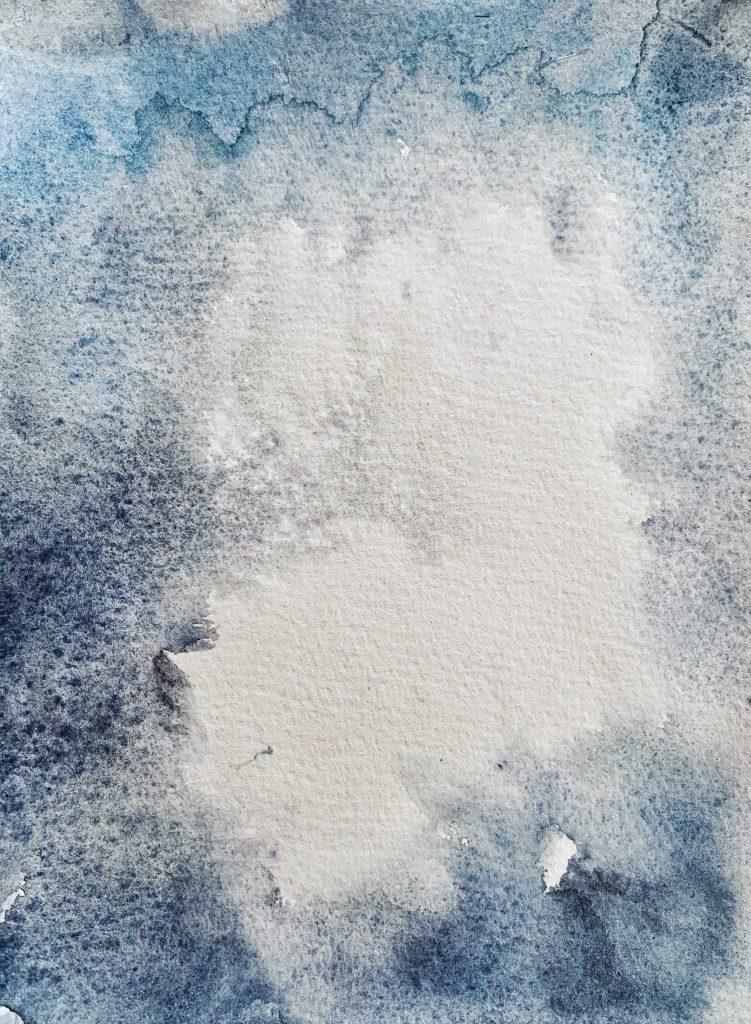The rise of a new nation
The rise of a new nation
「 比 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
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眾之歸而无咎。
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彖》曰:比,吉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甯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
——《周易本義[宋.朱熹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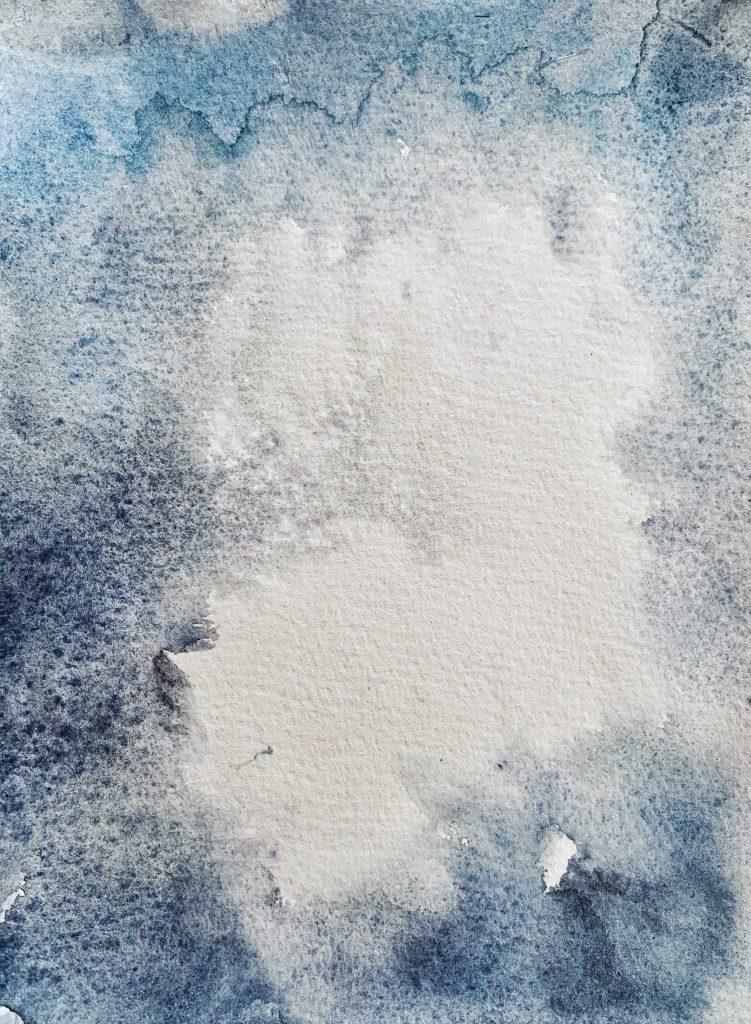 The rise of a new nation
The rise of a new nation
「那麼多個人家庭,付出了戰火傷亡的代價,將原先自然有機的社會群體,打造成一個系統效率的國家機器…那開國承家之後呢?」
「開國承家之後,就要建構讓自己說得上話,做得了事的國際關係網絡。」
「啊之前不是想參加一個人家辦的趴替,都要硬著頭皮渡河,厚著臉皮進場,人家還不一定讓妳進門?就算進了門,還只能在場邊待著,沒有說話的資格?」
「嗯,這叫做觀察員。」
「是不是?人家既然看不上我們,我們幹嘛巴著人家?」
「就是因為妳已經付出代價了,才不應該浪費代價,讓那些為國族創立付出生命者的犧牲,變得沒有意義。」
「那如何建構一個讓自己說得上話,做得了事的國際關係網絡?也開一個趴替嗎?」
「趴替是結果,不是原因。是妳擁有實力,人家都想來蹭妳的結果;沒有實力,妳只能開一個沒有賓客的淒涼宴會。」
「那實力從何而來?」
「實力要從佔據一個大家都對其有欲望的位置而來。」
「什麼意思?地理位置還是什麼嗎?」
「都有。
首先是地理位置,妳開建的國族天生就位於國際戰略要衝上,大家日常來往都要經過妳家門口,妳很難不重要。
其次是領域位置,妳們家在全球供應鍊中,有不可取代的關鍵角色,生產人家生產不出來,又都需要的物件,自然大家都會想找妳做生意。
最後是國際政治位置,那個拿妳當對手,非要把妳併吞否則嫌床不夠大睡覺睡不好的敵人,如果他愈大愈強,妳就會變得愈重要。」
「為什麼?敵人愈大愈強,我們不是愈倒霉,四處都交不到朋友嗎?」
「敵人愈大愈強,對其他國家威脅就愈大。這時他拿你當對手,就是告訴世界,妳是一個他害怕的關鍵,檯面上沒人敢跟妳說話,但回到座位上時,卻常會收到有人偷偷放的告白情書。」
「那如果上述三個要素我都俱備了呢?」
「那時間就在妳這邊,妳可以不慌不忙,依著世界進展的節奏,準備妳要開的趴替,想跟妳作朋友的人,會陸續進場。」
「那有些人就是不來呢?」
「那是他們的選擇,妳不用替他們擔心。妳此刻該關心的,是如何招呼好願意第一波跟妳交往的朋友,讓他們覺得冒得罪大國的風險值得。
至於那些晚來,乃至不來的,妳要用後續的事實證明,那是他們的損失。」
 The rise of a new nation
The rise of a new nation